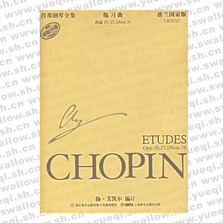肖邦作品原始版本的編輯所面對的遠(yuǎn)不是鑒定無數(shù)原始資料的簡單任務(wù)。即使能得到全部資料,也很難在簡單的瀏覽后確定相互間錯(cuò)綜復(fù)雜的關(guān)系。在這方面,莫里斯J.E.布洛的著作《肖邦――作品的年代次序索引》(倫敦,1960年)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幫助。
肖邦沒有以整套的意識來構(gòu)思他的練習(xí)曲(包括圓舞曲、瑪祖卡舞曲及夜曲等),只是在后來才把眾多不同時(shí)期創(chuàng)作的作品按類收集。作品系列的作品第10號和作品第25號就是按此法分類。
有些練習(xí)曲可能是間隔了很長時(shí)間才完成的,如作品第10號寫于1829年至1832年間,作品第25號寫于1832年至1836年間,另3首沒有作品號的寫于1839年。有些作品留有多種版本,隨后它們都被作曲家作為呈獻(xiàn)的作品。為此某首曲子就會存在數(shù)份手稿版本,每份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區(qū)別,結(jié)果,甚至連這些作品的手稿資料也不一致。
同樣很困難去收集不同的印刷版本。由于肖邦的經(jīng)營意識絕非一點(diǎn)沒有發(fā)展,他也安排很自己的作品在法國、德國和英國同時(shí)出版。雖然肖邦還總是信任抄譜員,但偶爾也會出現(xiàn)出版者為自己制作雕刻版的情況。如他的朋友朱里安?豐特納就因他的筆跡與肖邦有驚人的相似而著稱。
為此留給了后人一項(xiàng)鑒別個(gè)別抄譜員所寫的筆跡和判斷他們版本精確性的研究任務(wù)。在某種程度上,通過對不同國家出版的首版之間不同之處的對照也許對此有所幫助。
喬治?桑談到過肖邦非常細(xì)致謹(jǐn)慎的創(chuàng)作習(xí)慣。然而不應(yīng)忽視的是,他的敏感和異常即興的天才素質(zhì),使他總是易于受到油然而生和直覺創(chuàng)作沖動的影響。因此原稿資料所呈現(xiàn)的分歧不應(yīng)總是看成是錯(cuò)誤或者疏忽。他們也許來自于肖邦另一次的創(chuàng)作記錄。同樣,首版之間音樂上的不同不能都看作為雕刻制版過程中的錯(cuò)誤或疏忽。總是存在著這樣的可能,有另一份資料(也許你現(xiàn)在看不到)已經(jīng)作為某一雕刻版的原稿。由于原始資料的如此不確定性,所以不可能去確定在首版之間有多大的分歧,它們或許產(chǎn)生于對原稿深思熟慮的修改,亦可能是音樂上的變體。另一方面,因有如此廣泛的原始材料,在選擇特定文獻(xiàn)時(shí)個(gè)人喜好的指導(dǎo)因素會產(chǎn)生很大的影響,這與一致的原始資料的情況會有所不同。因此對于練習(xí)曲原始資料的收集是很困難的。
為了達(dá)到一個(gè)近乎一致的資料基礎(chǔ),編訂者已經(jīng)通過比較首版與雕刻版問那些發(fā)現(xiàn)在手稿中的(若不能總是,至少經(jīng)常能找到)記錄,試圖去發(fā)現(xiàn)該手稿是否已成為某一個(gè)首版的雕刻版的原稿。雖然這種努力只有部分成功,但它卻是收集和鑒定原始資料的一個(gè)可行辦法。這是在對現(xiàn)今版本做修訂的過程中總結(jié)出來的。例如,假如某部手稿作為某個(gè)首版的制版原稿的關(guān)系是明確的,或者是不確定的,那么對照手稿與首版間的一致或者任何變體.也許就能清楚是否是印刷排版上的錯(cuò)誤。但是,如果在手稿與首版之間沒有這種關(guān)系的證據(jù),那么首版中的不同之處很有可能起源于另一迄今未知的手稿,也有可能肖邦在出版者的制版完成之前對手稿作了某些有意的改動。在這些 情況下,有關(guān)哪些資料應(yīng)作為現(xiàn)今版本的基礎(chǔ)問題并不適應(yīng)于全部作品,而是每首曲子應(yīng)分開單獨(dú) 考慮。
作為作品第10號可得到的手稿,早期的第2首的抄本和第3至第12首的手稿可看作為肖邦的原稿,而第l首和第2首可能出自于肖邦的姐姐之手。通過雕刻版的注釋來判斷,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手稿第(3、6、8、10首)可能屬于由莫里斯?施萊辛格于1833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首版的原始資料(不是如潘德雷斯基聲稱的由勒穆瓦納編訂,他顯然用了后來的版本)。除上述資料還有另外的手稿參考材料也被作為此版本的基礎(chǔ)材料,其間的關(guān)系部分是確定的,還有的部分至少很像法國首版的原始材料。由基斯特納編訂的德國首版是與施萊辛格的緊密合作之下產(chǎn)生的。就第3首練習(xí)曲而言,除了上述資料,另有一份資料是紐約的R.O.萊曼收集的手稿可供參考。
對于作品第25號來說,根據(jù)華沙肖邦研究會的克雷斯塔納?科貝蘭斯卡所稱,只有現(xiàn)在的作品第25號波蘭手稿的第1首和第8首是原稿,而其余作品的手稿是豐特納或者其他抄譜員的抄本。由于波蘭的資料來自于布萊特科夫?哈特的檔案,他們可能也是1837年由布萊特科夫出版的德國首版的制版原搞。在此,兩個(gè)版本的原始資料倒是一致的。由雕刻師制作的五線譜部分與原稿一致,在德國首版中有少數(shù)例外(第3、6、7首),然而這是僅對第1至6首而言。到此為止,對于剩下的作品來說什么都沒發(fā)現(xiàn),所以,就第7至12首來說,如在標(biāo)題頁所示的,現(xiàn)今的版本是根據(jù)后來(1846年以后)的版本基礎(chǔ)上編訂的,并且因?yàn)榇嗽颍麄儾荒鼙豢醋鐾瑯拥臋?quán)威性。事實(shí)上,這個(gè)后來的版本可能是與首版結(jié)合的修訂本,這個(gè)德國首版的第二部分以及全部作品的法國首版,必定基于其他參考資料,所以只能有所保留地被參考。除了以上,還有另外的數(shù)份參考資料,如:第1首的另一份手稿,第2首的手稿,第4首的另一份手稿的1―20小節(jié)(以2/4拍子記譜)及第4首手稿的最后1―22小節(jié)。
肖邦創(chuàng)作了3首以“為技術(shù)而技術(shù)”的沒有作品號的練習(xí)曲,由莫施萊斯和費(fèi)蒂斯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。因此,供此版本所參考的手稿必定已作為雕刻版的原稿。而且這些練習(xí)曲出現(xiàn)在由同一個(gè)出版商于1841年出版的某一版本和柏林的A.M.施萊辛格的合集“鋼琴紀(jì)念冊”之中。
在編訂過程中,編者很明確上述材料的原始出處,并覺得更多的發(fā)現(xiàn)和修訂仍有可能。在這種
情況下,制定一個(gè)原始版本的任務(wù)要求考慮每首練習(xí)曲的各自情況。
相對于一般采用的G.亨勒’韋拉格的原始版本,相當(dāng)數(shù)量的原先指法以常見形式保留在此曲集中,那些由編輯所加的指法用斜體標(biāo)記。不僅主要資料的指法被保留,而且除少數(shù)例外的所有傳統(tǒng)指法同樣保留,因?yàn)樗鼈兇砹擞勺髑宜O(shè)定的重要的演奏指導(dǎo)。
那些很仔細(xì)地標(biāo)記在手稿中的踏板標(biāo)記,在編訂時(shí)僅取自于主要的材料,因?yàn)樵鹊奶ぐ蹇赡芤巡贿m應(yīng)于現(xiàn)代鋼琴的演奏(樂器更大、聲音更響、演奏廳更大)。今天,演奏者必須比資料中所標(biāo)的更頻繁地更換踏板,并且比起肖邦所標(biāo)記的,在演奏時(shí)需要在更多的段落使用踏板。有時(shí).快速的段落還需通過輕盈的觸鍵和模擬那個(gè)時(shí)代樂器的單薄音色來演釋。
至于資料中任何能夠清楚區(qū)分的不同斷奏記號(圓點(diǎn)與楔形),編訂者力圖保留原先的標(biāo)記。但是,原始資料中對這些記號的使用有時(shí)看來非常含混,在很多地方意圖不甚明確。在同一首練習(xí)曲中,對兩者的使用非常矛盾,有時(shí)模糊了兩者的區(qū)別。
編輯衷心感謝以下個(gè)人和機(jī)構(gòu)慷慨提供有關(guān)原稿資料的照片副本:巴黎的M.奧爾富萊德?科托特、倫敦的安東?赫德利先生、華沙的肖邦協(xié)會、紐約的歐內(nèi)斯特?謝林、瑞士的科克?弗洛什姆。編輯尤其感謝以下個(gè)人的各種信息和建議:維也納的包羅 巴杜拉一斯科達(dá)先生、華沙的克雷斯塔納?科貝蘭斯卡夫人和佐菲亞麗薩博士、德國的弗里德里希?布盧默博士和施呂赫特尼、英格蘭馬爾伯勒的莫里斯J E.布洛先生、巴黎的M弗拉基米爾費(fèi)奧多羅夫。
埃瓦爾德?齊默爾曼
(徐德譯文)
肖邦沒有以整套的意識來構(gòu)思他的練習(xí)曲(包括圓舞曲、瑪祖卡舞曲及夜曲等),只是在后來才把眾多不同時(shí)期創(chuàng)作的作品按類收集。作品系列的作品第10號和作品第25號就是按此法分類。
有些練習(xí)曲可能是間隔了很長時(shí)間才完成的,如作品第10號寫于1829年至1832年間,作品第25號寫于1832年至1836年間,另3首沒有作品號的寫于1839年。有些作品留有多種版本,隨后它們都被作曲家作為呈獻(xiàn)的作品。為此某首曲子就會存在數(shù)份手稿版本,每份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區(qū)別,結(jié)果,甚至連這些作品的手稿資料也不一致。
同樣很困難去收集不同的印刷版本。由于肖邦的經(jīng)營意識絕非一點(diǎn)沒有發(fā)展,他也安排很自己的作品在法國、德國和英國同時(shí)出版。雖然肖邦還總是信任抄譜員,但偶爾也會出現(xiàn)出版者為自己制作雕刻版的情況。如他的朋友朱里安?豐特納就因他的筆跡與肖邦有驚人的相似而著稱。
為此留給了后人一項(xiàng)鑒別個(gè)別抄譜員所寫的筆跡和判斷他們版本精確性的研究任務(wù)。在某種程度上,通過對不同國家出版的首版之間不同之處的對照也許對此有所幫助。
喬治?桑談到過肖邦非常細(xì)致謹(jǐn)慎的創(chuàng)作習(xí)慣。然而不應(yīng)忽視的是,他的敏感和異常即興的天才素質(zhì),使他總是易于受到油然而生和直覺創(chuàng)作沖動的影響。因此原稿資料所呈現(xiàn)的分歧不應(yīng)總是看成是錯(cuò)誤或者疏忽。他們也許來自于肖邦另一次的創(chuàng)作記錄。同樣,首版之間音樂上的不同不能都看作為雕刻制版過程中的錯(cuò)誤或疏忽。總是存在著這樣的可能,有另一份資料(也許你現(xiàn)在看不到)已經(jīng)作為某一雕刻版的原稿。由于原始資料的如此不確定性,所以不可能去確定在首版之間有多大的分歧,它們或許產(chǎn)生于對原稿深思熟慮的修改,亦可能是音樂上的變體。另一方面,因有如此廣泛的原始材料,在選擇特定文獻(xiàn)時(shí)個(gè)人喜好的指導(dǎo)因素會產(chǎn)生很大的影響,這與一致的原始資料的情況會有所不同。因此對于練習(xí)曲原始資料的收集是很困難的。
為了達(dá)到一個(gè)近乎一致的資料基礎(chǔ),編訂者已經(jīng)通過比較首版與雕刻版問那些發(fā)現(xiàn)在手稿中的(若不能總是,至少經(jīng)常能找到)記錄,試圖去發(fā)現(xiàn)該手稿是否已成為某一個(gè)首版的雕刻版的原稿。雖然這種努力只有部分成功,但它卻是收集和鑒定原始資料的一個(gè)可行辦法。這是在對現(xiàn)今版本做修訂的過程中總結(jié)出來的。例如,假如某部手稿作為某個(gè)首版的制版原稿的關(guān)系是明確的,或者是不確定的,那么對照手稿與首版間的一致或者任何變體.也許就能清楚是否是印刷排版上的錯(cuò)誤。但是,如果在手稿與首版之間沒有這種關(guān)系的證據(jù),那么首版中的不同之處很有可能起源于另一迄今未知的手稿,也有可能肖邦在出版者的制版完成之前對手稿作了某些有意的改動。在這些 情況下,有關(guān)哪些資料應(yīng)作為現(xiàn)今版本的基礎(chǔ)問題并不適應(yīng)于全部作品,而是每首曲子應(yīng)分開單獨(dú) 考慮。
作為作品第10號可得到的手稿,早期的第2首的抄本和第3至第12首的手稿可看作為肖邦的原稿,而第l首和第2首可能出自于肖邦的姐姐之手。通過雕刻版的注釋來判斷,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手稿第(3、6、8、10首)可能屬于由莫里斯?施萊辛格于1833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首版的原始資料(不是如潘德雷斯基聲稱的由勒穆瓦納編訂,他顯然用了后來的版本)。除上述資料還有另外的手稿參考材料也被作為此版本的基礎(chǔ)材料,其間的關(guān)系部分是確定的,還有的部分至少很像法國首版的原始材料。由基斯特納編訂的德國首版是與施萊辛格的緊密合作之下產(chǎn)生的。就第3首練習(xí)曲而言,除了上述資料,另有一份資料是紐約的R.O.萊曼收集的手稿可供參考。
對于作品第25號來說,根據(jù)華沙肖邦研究會的克雷斯塔納?科貝蘭斯卡所稱,只有現(xiàn)在的作品第25號波蘭手稿的第1首和第8首是原稿,而其余作品的手稿是豐特納或者其他抄譜員的抄本。由于波蘭的資料來自于布萊特科夫?哈特的檔案,他們可能也是1837年由布萊特科夫出版的德國首版的制版原搞。在此,兩個(gè)版本的原始資料倒是一致的。由雕刻師制作的五線譜部分與原稿一致,在德國首版中有少數(shù)例外(第3、6、7首),然而這是僅對第1至6首而言。到此為止,對于剩下的作品來說什么都沒發(fā)現(xiàn),所以,就第7至12首來說,如在標(biāo)題頁所示的,現(xiàn)今的版本是根據(jù)后來(1846年以后)的版本基礎(chǔ)上編訂的,并且因?yàn)榇嗽颍麄儾荒鼙豢醋鐾瑯拥臋?quán)威性。事實(shí)上,這個(gè)后來的版本可能是與首版結(jié)合的修訂本,這個(gè)德國首版的第二部分以及全部作品的法國首版,必定基于其他參考資料,所以只能有所保留地被參考。除了以上,還有另外的數(shù)份參考資料,如:第1首的另一份手稿,第2首的手稿,第4首的另一份手稿的1―20小節(jié)(以2/4拍子記譜)及第4首手稿的最后1―22小節(jié)。
肖邦創(chuàng)作了3首以“為技術(shù)而技術(shù)”的沒有作品號的練習(xí)曲,由莫施萊斯和費(fèi)蒂斯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。因此,供此版本所參考的手稿必定已作為雕刻版的原稿。而且這些練習(xí)曲出現(xiàn)在由同一個(gè)出版商于1841年出版的某一版本和柏林的A.M.施萊辛格的合集“鋼琴紀(jì)念冊”之中。
在編訂過程中,編者很明確上述材料的原始出處,并覺得更多的發(fā)現(xiàn)和修訂仍有可能。在這種
情況下,制定一個(gè)原始版本的任務(wù)要求考慮每首練習(xí)曲的各自情況。
相對于一般采用的G.亨勒’韋拉格的原始版本,相當(dāng)數(shù)量的原先指法以常見形式保留在此曲集中,那些由編輯所加的指法用斜體標(biāo)記。不僅主要資料的指法被保留,而且除少數(shù)例外的所有傳統(tǒng)指法同樣保留,因?yàn)樗鼈兇砹擞勺髑宜O(shè)定的重要的演奏指導(dǎo)。
那些很仔細(xì)地標(biāo)記在手稿中的踏板標(biāo)記,在編訂時(shí)僅取自于主要的材料,因?yàn)樵鹊奶ぐ蹇赡芤巡贿m應(yīng)于現(xiàn)代鋼琴的演奏(樂器更大、聲音更響、演奏廳更大)。今天,演奏者必須比資料中所標(biāo)的更頻繁地更換踏板,并且比起肖邦所標(biāo)記的,在演奏時(shí)需要在更多的段落使用踏板。有時(shí).快速的段落還需通過輕盈的觸鍵和模擬那個(gè)時(shí)代樂器的單薄音色來演釋。
至于資料中任何能夠清楚區(qū)分的不同斷奏記號(圓點(diǎn)與楔形),編訂者力圖保留原先的標(biāo)記。但是,原始資料中對這些記號的使用有時(shí)看來非常含混,在很多地方意圖不甚明確。在同一首練習(xí)曲中,對兩者的使用非常矛盾,有時(shí)模糊了兩者的區(qū)別。
編輯衷心感謝以下個(gè)人和機(jī)構(gòu)慷慨提供有關(guān)原稿資料的照片副本:巴黎的M.奧爾富萊德?科托特、倫敦的安東?赫德利先生、華沙的肖邦協(xié)會、紐約的歐內(nèi)斯特?謝林、瑞士的科克?弗洛什姆。編輯尤其感謝以下個(gè)人的各種信息和建議:維也納的包羅 巴杜拉一斯科達(dá)先生、華沙的克雷斯塔納?科貝蘭斯卡夫人和佐菲亞麗薩博士、德國的弗里德里希?布盧默博士和施呂赫特尼、英格蘭馬爾伯勒的莫里斯J E.布洛先生、巴黎的M弗拉基米爾費(fèi)奧多羅夫。
埃瓦爾德?齊默爾曼
(徐德譯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