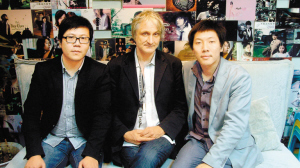僅就“新年音樂會”這一特定概念而言,祖賓?梅塔指揮的以色列愛樂樂團2007年12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演出所給予我們的已經(jīng)比維也納金色大廳多得多!
首先是“新年音樂會”的特定日子,在中國有“迎新”的傳統(tǒng),“除夕”肯定更被重視;其次是演出場所,有近七千個座位的人民大會堂雖然存在不可克服的音響缺陷,但它作為中國“最高慶典會堂”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;其三是音樂會的主角―――指揮和樂團,曾經(jīng)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新年音樂會登臺的指揮家在中國指揮新年音樂會,迄今為止,只有梅塔和小澤征爾,2005年時,梅塔是第一個,今年則形成“雙雄決戰(zhàn)紫禁之巔”的局面,梅塔在人民大會堂指揮以色列愛樂,同一時間在隔壁的國家大劇院,小澤征爾指揮中國交響樂團聯(lián)袂郎朗、列賓和巴特爾奉獻一場并無新意的節(jié)日慶典。
為何說這樣的節(jié)日慶典并無新意?這就是我要說的“其四”的內(nèi)容―――曲目。自從“新年音樂會”被引進中國以來,年復(fù)一年做得很累效果卻總是差強人意的原因就在于這個力求“五臟俱全”的節(jié)日慶典上。從觀眾的角度,希望看到琳瑯滿目的內(nèi)容,但從主辦者角度則會在每年的提高突破方面大傷腦筋。節(jié)日慶典的基本要求是“群星輝映”,而所謂的“群星輝映”需要有個平衡度,指揮、歌手、獨奏家,甚至樂團一定是聲望接近,水平相差無幾,能夠達到這一簡單平衡的GALA其實在中國的“新年音樂會”上始終沒有出現(xiàn)過。
之所以為梅塔2005年的北京新年音樂會喝彩,其中較重要的理由便是我在“新年音樂會”上同時享受了純粹的音樂與節(jié)日的歡樂,那既不是金色大廳施特勞斯家族盛宴的拷貝,也非你方唱罷我登場的“拼盤”。梅塔和以色列愛樂始終是音樂會的主角,他們呈現(xiàn)的是最能彰顯指揮和樂團風格的馬勒和里姆斯基-科薩柯夫,是勃拉姆斯和德沃夏克,施特勞斯僅僅作為“日場”的點綴,卻也如珠玉般晶瑩璀璨,盡現(xiàn)光彩。
今年的梅塔新年音樂會曲目仍然完整而有特色,上半場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“來自新世界”,下半場是三首維也納類型作品加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莊嚴序曲》。特別應(yīng)當指出的是,為即將到來的北京奧運會而演奏的“開場曲”《奧林匹克號角》由梅塔指揮也別具意義。首先作曲家約翰?威廉斯是梅塔的老搭檔,他們合作的《星球大戰(zhàn)》電影配樂膾炙人口,經(jīng)典地位無可撼動。同樣梅塔也得過威廉斯的現(xiàn)場協(xié)助,錄制過《奧林匹克號角》的唱片,他是當之無愧這首激昂蓬勃的“鼓號樂”的權(quán)威演繹者!也就是說,我們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聽過的此曲以這次“人民大會堂版”為“真身正宗”。
為了“北京”的概念,梅塔為北京新年音樂會的聽眾獻上了一曲《紅旗頌》。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決非偶然,因為他們聽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“自己的”音樂,聽到了前所未聞的音樂境界大大提升的“紅色經(jīng)典”。盡管排練時間非常有限,但是梅塔和以色列愛樂的樂師們找到了樂曲的核心,掌握了主題的胚胎及衍生的邊際,他們創(chuàng)作性地擴展了音響的層次,重新劃定力量動態(tài)的分配,甚至在速率上作了些微變化,最終使《紅旗頌》在精神層面不再單一粗放,在情緒上渾厚飽滿,漸顯多元。在昨夜的聆聽中,我聽到被刻意放大的源于“國歌”的主題雛形,它的悲壯意味十分顯著,如警鐘長鳴般在整部作品的空間里無所不在。梅塔和以色列愛樂的音樂家們在《紅旗頌》當中體現(xiàn)的充沛激情和全力以赴的職業(yè)精神,賦予這首中國作品以全新的狀貌,同時被其輝煌激越的氣派所激發(fā)引導(dǎo),共同呈現(xiàn)出令人蕩氣回腸,意氣風發(fā)的華彩樂章。
欣賞這樣一位超級指揮大師和世界排名靠前的優(yōu)秀樂團的音樂會,一部完整的大型交響樂是必不可少的。2005年是馬勒的第一交響曲和里姆斯基-科薩柯夫的《天方夜譚》,這次是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,如果算上前一天演出的理查?施特勞斯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,可以說這次梅塔和以色列愛樂仍然是“不虛此行”,北京的聽眾無論如何挑剔,都必須承認“大飽耳福”的事實。如果說他們演奏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已經(jīng)近乎完美,那么我所聽到的《蝙蝠序曲》和加演的《斯拉夫舞曲》、《達夫尼與赫洛埃》第二組曲的“終曲”便可謂臻于演繹的化境,特別是《蝙蝠序曲》在節(jié)奏上的大膽變化以及力度的微妙處理,都使喜劇效果之上更添趣味,新意盎然。拉威爾的音樂一直是梅塔個人興味所在,雖少見唱片問世,但一直是他音樂會的常見曲目,這次能在“安可”當中驚現(xiàn)“靈光一瞥”,讓從未聽過此曲的人也如醍醐灌頂,眼前豁然明亮。能夠把拉威爾的音樂在色彩和力量,層次與結(jié)構(gòu)方面取得如此完美統(tǒng)一的指揮家,當今世界已是極其罕見!
我曾在2005年的文章里指出梅塔與以色列愛樂樂團為走過10年歷程的“北京新年音樂會”確立了一個難以逾越的制高點。在我的預(yù)期當中,除非全能的維也納愛樂和柏林愛樂肯屈尊前來,否則梅塔與以色列愛樂的“新年音樂會”將作為一個紀錄一直保持下去。可喜的是,這個紀錄被創(chuàng)造這個紀錄的自身在三年內(nèi)即告跨越,雖然幅度不是很大,卻由于相關(guān)運營制作的水準顯著提升,特別是舞臺布置和音響條件大大改善,在總體上實現(xiàn)了階段性發(fā)展。
首先是“新年音樂會”的特定日子,在中國有“迎新”的傳統(tǒng),“除夕”肯定更被重視;其次是演出場所,有近七千個座位的人民大會堂雖然存在不可克服的音響缺陷,但它作為中國“最高慶典會堂”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;其三是音樂會的主角―――指揮和樂團,曾經(jīng)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新年音樂會登臺的指揮家在中國指揮新年音樂會,迄今為止,只有梅塔和小澤征爾,2005年時,梅塔是第一個,今年則形成“雙雄決戰(zhàn)紫禁之巔”的局面,梅塔在人民大會堂指揮以色列愛樂,同一時間在隔壁的國家大劇院,小澤征爾指揮中國交響樂團聯(lián)袂郎朗、列賓和巴特爾奉獻一場并無新意的節(jié)日慶典。
為何說這樣的節(jié)日慶典并無新意?這就是我要說的“其四”的內(nèi)容―――曲目。自從“新年音樂會”被引進中國以來,年復(fù)一年做得很累效果卻總是差強人意的原因就在于這個力求“五臟俱全”的節(jié)日慶典上。從觀眾的角度,希望看到琳瑯滿目的內(nèi)容,但從主辦者角度則會在每年的提高突破方面大傷腦筋。節(jié)日慶典的基本要求是“群星輝映”,而所謂的“群星輝映”需要有個平衡度,指揮、歌手、獨奏家,甚至樂團一定是聲望接近,水平相差無幾,能夠達到這一簡單平衡的GALA其實在中國的“新年音樂會”上始終沒有出現(xiàn)過。
之所以為梅塔2005年的北京新年音樂會喝彩,其中較重要的理由便是我在“新年音樂會”上同時享受了純粹的音樂與節(jié)日的歡樂,那既不是金色大廳施特勞斯家族盛宴的拷貝,也非你方唱罷我登場的“拼盤”。梅塔和以色列愛樂始終是音樂會的主角,他們呈現(xiàn)的是最能彰顯指揮和樂團風格的馬勒和里姆斯基-科薩柯夫,是勃拉姆斯和德沃夏克,施特勞斯僅僅作為“日場”的點綴,卻也如珠玉般晶瑩璀璨,盡現(xiàn)光彩。
今年的梅塔新年音樂會曲目仍然完整而有特色,上半場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“來自新世界”,下半場是三首維也納類型作品加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莊嚴序曲》。特別應(yīng)當指出的是,為即將到來的北京奧運會而演奏的“開場曲”《奧林匹克號角》由梅塔指揮也別具意義。首先作曲家約翰?威廉斯是梅塔的老搭檔,他們合作的《星球大戰(zhàn)》電影配樂膾炙人口,經(jīng)典地位無可撼動。同樣梅塔也得過威廉斯的現(xiàn)場協(xié)助,錄制過《奧林匹克號角》的唱片,他是當之無愧這首激昂蓬勃的“鼓號樂”的權(quán)威演繹者!也就是說,我們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聽過的此曲以這次“人民大會堂版”為“真身正宗”。
為了“北京”的概念,梅塔為北京新年音樂會的聽眾獻上了一曲《紅旗頌》。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決非偶然,因為他們聽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“自己的”音樂,聽到了前所未聞的音樂境界大大提升的“紅色經(jīng)典”。盡管排練時間非常有限,但是梅塔和以色列愛樂的樂師們找到了樂曲的核心,掌握了主題的胚胎及衍生的邊際,他們創(chuàng)作性地擴展了音響的層次,重新劃定力量動態(tài)的分配,甚至在速率上作了些微變化,最終使《紅旗頌》在精神層面不再單一粗放,在情緒上渾厚飽滿,漸顯多元。在昨夜的聆聽中,我聽到被刻意放大的源于“國歌”的主題雛形,它的悲壯意味十分顯著,如警鐘長鳴般在整部作品的空間里無所不在。梅塔和以色列愛樂的音樂家們在《紅旗頌》當中體現(xiàn)的充沛激情和全力以赴的職業(yè)精神,賦予這首中國作品以全新的狀貌,同時被其輝煌激越的氣派所激發(fā)引導(dǎo),共同呈現(xiàn)出令人蕩氣回腸,意氣風發(fā)的華彩樂章。
欣賞這樣一位超級指揮大師和世界排名靠前的優(yōu)秀樂團的音樂會,一部完整的大型交響樂是必不可少的。2005年是馬勒的第一交響曲和里姆斯基-科薩柯夫的《天方夜譚》,這次是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,如果算上前一天演出的理查?施特勞斯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,可以說這次梅塔和以色列愛樂仍然是“不虛此行”,北京的聽眾無論如何挑剔,都必須承認“大飽耳福”的事實。如果說他們演奏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已經(jīng)近乎完美,那么我所聽到的《蝙蝠序曲》和加演的《斯拉夫舞曲》、《達夫尼與赫洛埃》第二組曲的“終曲”便可謂臻于演繹的化境,特別是《蝙蝠序曲》在節(jié)奏上的大膽變化以及力度的微妙處理,都使喜劇效果之上更添趣味,新意盎然。拉威爾的音樂一直是梅塔個人興味所在,雖少見唱片問世,但一直是他音樂會的常見曲目,這次能在“安可”當中驚現(xiàn)“靈光一瞥”,讓從未聽過此曲的人也如醍醐灌頂,眼前豁然明亮。能夠把拉威爾的音樂在色彩和力量,層次與結(jié)構(gòu)方面取得如此完美統(tǒng)一的指揮家,當今世界已是極其罕見!
我曾在2005年的文章里指出梅塔與以色列愛樂樂團為走過10年歷程的“北京新年音樂會”確立了一個難以逾越的制高點。在我的預(yù)期當中,除非全能的維也納愛樂和柏林愛樂肯屈尊前來,否則梅塔與以色列愛樂的“新年音樂會”將作為一個紀錄一直保持下去。可喜的是,這個紀錄被創(chuàng)造這個紀錄的自身在三年內(nèi)即告跨越,雖然幅度不是很大,卻由于相關(guān)運營制作的水準顯著提升,特別是舞臺布置和音響條件大大改善,在總體上實現(xiàn)了階段性發(fā)展。
更多: